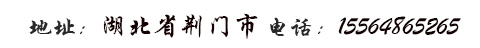驻外手账新西兰来套中国的煎饼果子
|
白癜风有啥外用药 http://news.39.net/bjzkhbzy/180502/6205113.html 市场是个有趣的东西。鲁迅当年写“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现在,我也大致能理解他心里的感受。 1最近,新西兰一家超级企业把旗下冰激凌通过某宝卖到国内,2升装标价至元人民币不等。我略有不忿,因为同样产品在新西兰只卖4块多,折合人民币不到20块钱。 学市场营销的宁博士,三十大几、学位未遂,素来喜欢跟我争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次,他终于逮住教育我的机会,讲一堆“原产国本身就是定位,有天然或人为稀缺性”之类的理论。隔行如隔山,我也懒得继续辩。 还是内子说得对:“有人卖,有人买,关你们两个穷鬼什么事?!” 想起从前在比利时上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布鲁塞尔小卷心菜。在新西兰,没少听人吐槽这东西有多难吃。其实,这种略略发苦的菜只要对切,少用点黄油煎焦边缘,就去掉了那种苦味。 不过,这菜在国内的宣传中成为“甘蓝类蔬菜之首”,售价昂贵,着实吃不起。用比普通甘蓝贵得多的价钱去买可能堪比“神药”的小卷心菜?至少我这种“穷鬼”没那么大魄力。 数月前,新西兰有一场母婴用品展销会,产品种类丰富,从零食到蹦床、从奶粉到安全座椅,大开眼界。恰好表姐怀孕,就顺手买了奶瓶作为给未来小外甥的礼物,一套四只,还有几个可爱的奶嘴,折合人民币出头。 因为是欧洲产的,本以为漂洋过海到新西兰、到中国价格应该差不多。但在某宝上搜同款,国内的价格却五花八门,最便宜不到,最贵的0冒头。 我没有孩子,暂时没法完全体会父母可以为孩子不计代价的情感倾注。但外国的奶瓶是不是比中国好,是不是一定符合中国产品标准和中国孩子的体质,这些问题恐怕只能请教专家了。但专家说的真都客观么? 2 内子无聊时,到新西兰一家当地出名的咖啡馆学Barista。捧着证书学成归来,很有仪式感地做了一杯奶泡咖啡,结果我没看到什么精美的拉花,连基本款的叶子和心形拉花也都有些杜尚的风格。问原因,得了一句“没品位”的考语。 原来,Barista的重点不是拉花,而是奶泡、咖啡和牛奶三者完美的融合,期间又如牛奶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在65摄氏度等细致入微的讲究。至于拉花,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炫技,好咖啡不一定有好拉花,拉花好也不代表咖啡好。 内子去的这家咖啡馆也在中国开了店,就在西安北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咖啡馆都主打“小白咖啡(FlatWhite)”,究竟是谁发明的是两个国扯来扯去说不清的公案。 参考星某克的价格定位,“小白咖啡”大概是30块钱,只不过是改了名字,叫做“馥芮白”,而这东西在新西兰的售价大概折合人民币20多,不算离谱。 能喝到价格并不离谱的咖啡,也许应该感谢星某克这种国际连锁。无论是有心还是可观,星某克做到了一点,就是给咖啡“祛魅”,让它回归一种普通饮品,而不像在缅甸只有五星级酒店大堂里才卖得出一杯体面的特浓咖啡。 新西兰也有星某克,也在那些写字楼附近出没,可在新西兰人眼中,大型连锁咖啡馆就像黄渤说得是个街头的“牌子”,算不了档次之选。 他们喜欢的是海边或山脚,某家愿意自己四处攒豆子混合烘焙的私家店主,最好还有一句“百分百新西兰创造”。 这种想法能不能出口到中国?我不知道。 3 在北京上班时,特别喜欢吃一对本地夫妻在盆儿胡同卖的煎饼果子,每天早上都有一群上班族在那里排队。内子有时下班晚,早上想要多睡会,我就提前出去交钱排队。 那对夫妻分工明确,妻子摊煎饼,丈夫就在一旁收钱并向排队的人提供侃大山服务。他告诉我,自己就住在旁边的小区,和妻子每天下午当着街坊邻居的面儿炸薄脆,每天用一桶附近超市买的新油,和面也是按照传说中最正宗的天津配方,所以保证既好吃又安全放心。 喜欢跟这位北京大叔聊天,他除了给自己的煎饼做广告,几乎什么话题都愿聊几句。大叔似乎不算担心北京的雾霾,倒是说起国际新闻里哪里爆炸、哪里袭击的时候特有感触,一定要说一句“还是咱这里安全啊”。 为了提神,上班每每带杯黑咖啡。吃了满口香菜葱花的煎饼果子,喝一口去油消腻的咖啡,顿时精神满满,觉得相声里说大蒜就咖啡颇有道理。 到了新西兰,多多少少还是会怀念下北京大叔的煎饼。眼看着华人移民数量增加,不少城市也能吃到煎饼,只是味道不那么道地。有时摊煎饼面糊过多,有时隔夜油条咬不动,有时候薄脆没经过复炸太油腻。 可这里煎饼的价格数目却和北京大叔一致,乘上接近5倍的汇率差,吃煎饼也变成一件略有点肉疼的事情。这让我午夜梦回总是想向北京大叔介绍一下新西兰煎饼市场的前景。 到了国外,煎饼也被扎上了“红头绳”、请进了“温室”,还拥有了多种多样的“变身”,可以夹带培根、香肠,连酱料也可以换成蛋黄酱“美乃滋”,就好似美国上校爷爷在南亚卖咖喱味的米饭。 当然,煎饼并没有什么“新西兰统一价”,华人多的地方就便宜一些,华人少的地方就贵一些,华人再少的地方就没得卖,就好像榨菜和松花蛋一样。这件事很符合逻辑,因为消费的人多是华人。洋人愿意尝尝鲜,但也就把煎饼当成是印度的抛饼或土耳其的kebab,不像我们眼中的布鲁塞尔卷心菜,还得“祛魅”。 4 发现自己很喜欢用“祛魅”这个词。这似乎不算太恰当,因为“祛魅”实在是一个过于宏观的概念,但马克斯·韦伯也说“祛魅”意味着更理智化。或者也可以换一个词,叫做“脱敏”,让钱包减少一些对于“外国月亮”的敏感。 这年头,同胞多笃信市场的力量,坚持“看不见的手”。社里的刊物曾约稿,希望了解新西兰的乳业发展。 说实话,中国牧业最难跨越的障碍可能不是外国的商业竞争,而是“看不见的人心”。别说牛奶,在中国土地上种出来的甘蓝类小卷心菜,如果贴上布鲁塞尔品种的名头,恐怕也会比普通甘蓝贵出不少。 不是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像咖啡一样通过连锁的星某克“祛魅”,如果无法理性看待消费品,“看不见的人心”会像“看不见的手”一样,左右市场。 当然,这种“脱敏”也应该笃信市场的方式,如何提升对“中国出产”的信心,并不是我和卖煎饼果子的北京大叔侃大山时能得出结论的事情。 5 后来,我还是在新西兰发现了好吃的煎饼果子,就在克莱斯特彻奇华人聚集的地方,缩在路口喧嚣中的一个小门脸。 地震了,屋子地板晃动的时候也肝儿颤,后来忙活完了有机会咬一口煎饼果子,还是有些小感动。 生,而活着,不管在哪儿,都是那套吃喝拉撒的烟火气儿。 什么?多少钱一套?管它呢。 -END- 作者宿亮,国际政治学博士,曾就读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年入职新华社国际部,年任惠灵顿分社记者。 监制:李大伟 编辑:陈杉刘一楠 图片来自宿亮及网络 如果喜欢这类文章,欢迎长按识别下图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nxilanhaishi.com/xxlhswxtz/9102.html
- 上一篇文章: 12款奶粉深度评测哪款配方更
- 下一篇文章: 高血压的真相预防和调理海狗油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