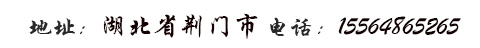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身边的聪明人都喜欢玩,且玩的很
|
特约编辑/大路 19世纪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兹曾有个形象的比喻,他把解决难题比作爬山,“一个登山者或许常常会因为前面没有路了,而不得不走回头路。而当这个登山者撞见一条新路痕迹的时候,或许才会恍然大悟,这条新路才是通往顶峰的路"。这位物理学家的反省引发了一个问题。如何用创造性思维去克服“山谷”,到达下一个高峰呢? 因为我们的思维不同于不断进化的有机体和自动形成的分子,我们不能指望它使用同样的手段--基因漂变和热振动等机制来克服它们探索的风景中的深谷。但它一定有某种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事实证明,它的方法不止一种,还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游戏。 这里的游戏,指的不是棋盘游戏中基于规则的游戏,也不是足球比赛中的竞争性游戏,而是孩子们用一堆乐高积木或用玩具铲和桶在沙箱中进行的那种自由自在、无组织的游戏。对这种没有直接目标和利益,甚至没有失败可能性的游戏行为,或许我们该称之为玩耍。 动物都很贪玩这种玩耍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大自然在发明我们之前就发明了玩耍。几乎所有年轻的哺乳动物都会玩耍,当然鹦鹉和乌鸦等鸟类也是如此。爬行动物、鱼类甚至蜘蛛也有玩耍的行为,甚至还未成熟的动物会利用玩耍来练习交配。但动物游戏的世界玩耍冠军可能是瓶鼻海豚,有37种不同类型的玩耍行为。圈养的海豚会不厌其烦地玩球和其他玩具,而野生海豚则会玩羽毛、海绵等物体,以及它们从吹气孔中挤出的气泡"圈圈"。 几乎所有动物都有广泛意义上的玩耍,这一定不仅仅是大自然的偶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玩耍是要付出成本的!年轻的动物得花费高达20%的日常能量来玩耍,而不是去准备他们的晚餐。并且,它们的玩耍有时还会造成严重的问题。玩耍中的猎豹幼崽常常会吓跑他们妈妈的猎物,大象有时会因玩耍被卡在泥里,而大角羊也会因贪玩被仙人掌刺伤。有些贪玩的动物甚至会因此失去生命。在年的一项研究中,剑桥大学的研究员罗伯特-哈考特持续观察了南美毛皮海豹的一个群落。在一个季节内,该群落的只幼崽被海狮攻击,其中26只幼崽被杀死。被杀的幼崽中,80%以上是在玩耍时被攻击的。 成本这么高,肯定也是有效益的。事实上,玩耍的好处甚至也关乎生死。例如,新西兰的野马玩得越多,它们第一年的存活率就越高。同样,阿拉斯加棕熊幼崽在第一个夏天玩得越多,不仅能更好地度过第一个冬天,而且在以后的冬天也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雄性蜘蛛甚至会去练习如何快速交配,以便能在其他雄性蜘蛛攻击它们之前逃离。 这种玩耍当然也不是单纯为了开心。当马儿玩耍时,肌肉会得到增强,而这种力量可以帮助它们生存。当幼狮嬉戏打闹时,它们是在为真正的打斗做准备,而这种打斗将帮助它们主宰群体。当海豚玩弄气泡时,它们其实是在磨练迷惑和捕捉猎物的技巧。 至少在哺乳动物中,玩耍不仅仅是一种老套的练习行为,像钢琴家反复排练同一段落一样。当哺乳动物潜行、捕猎和逃跑时,它们总会发现自己处于新的情境和环境中。而游戏扩大了动物的行为方式,使它们能够灵活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换句话说,动物通过玩耍创造了多样化的行为,不管这种多样性是否立即有用,都可使玩耍者在一个不可预知的世界里为意外情况做好准备。这种多样灵活性也能帮助动物解决难题。年的一个实验证明了玩耍对幼鼠的价值。在这个实验中,一些老鼠与同伴被笼子里的网眼隔离了20天,这使得它们无法玩耍。隔离期过后,研究人员教所有的老鼠通过拉出一个橡胶球来获得食物奖励。然后,他们将任务改换,幼鼠必须推球,而不是拉。与自由玩耍的同伴相比,游戏匮乏的老鼠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尝试,意识到这种新的获取食物的方法。 剑桥大学伦理学家帕特里克-贝特森更将这样的观察结果与创造性直接联系起来,他认为玩耍可以"实现探索的作用,使个体能够从错误的终点,或局部的选择点中逃脱出来","当卡在一个隐喻的低峰上时,有积极的机制来摆脱它,登上一个更高的高峰,这是他的价值所在的"。在这种观点中,玩耍之于创造力,就像基因漂变之于进化,热能之于自组装分子一样。 天才都爱“玩”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创造力的人经常把他们的工作描述为“玩乐”就不足为奇了。发现青霉素的亚历山大-弗莱明,就常常因为他的玩闹态度而受到过老板的责备。他说:"我玩弄微生物......。打破常规,发现一些没有人想到的东西是非常愉快的。"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安德烈-盖姆也宣称:"这种玩乐的态度一直是我研究事物的特点......。除非你碰巧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间,或者你拥有别人没有的特性,否则唯一的办法就是更加冒险。"当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双螺旋时,他们也是从玩乐中得到了灵感,他们把彩球粘在一起--像乐高一样--建立了一个模型。用沃森的话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开始玩"。 玩耍的一个特点是它能暂停判断,使我们不再专注于选择好的想法和摒弃坏的想法。这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不完美的山谷,然后再攀登完美的高峰的原因。 我们的梦境相对来说,不那么刻意但同样有影响力。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Piaget)将做梦也比作玩耍,他的开创性研究帮助我们了解了儿童的发育。正是在梦中,我们的大脑最自由地将最奇异的思想和图像碎片组合成新颖的人物和情节。保罗-麦卡特尼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他第一次在梦中听到自己的歌曲《昨天》,不相信这是一首原创歌曲,事后几周都在问音乐界的人是否知道。他们都不知道。《昨天》这首歌成为了20世纪最成功的歌曲之一,共演出万场,翻唱版本超过个。 另一个梦境也悄悄地启发了德国生理学家奥托-勒维一个关键性实验的想法,它证明了神经通过化学物质进行交流,我们现在称之为神经递质。这个发现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心理学家称之为入眠期--我们的思想会足够松散,可以去展开任何想象,而不受制于经验的印象。 在这种状态下,奥古斯特-凯库勒看到了苯的结构,玛丽-雪莱找到了她标志性小说《弗兰肯斯坦》的构思,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表。 与玩耍和做梦相似的是我们的思维放飞。96%的美国成年人报告说,他们每天都会走神--另外4%的人可能因心不在焉而没有注意到。其实要量化任何一个人在任务过程中走神的频率很简单---直接问就可以了。去打断正在工作的人,问他们在想什么。或者用手机给研究参与者发一条短信,在随机时间去问他们在想什么。当心理学家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发现走神的频率是惊人的。典型的走神时间在三分之一到一半之间。 走神是有好有坏的。让我们从坏的开始说起,经常心不在焉的人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测试中通常表现较差,比如阅读理解测试。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在考试中的表现也更差。 但是,走神也有一个好处--至少对于太过专注的人来说是这样。事实上,在许多创造者的轶事中,如爱因斯坦、牛顿和著名数学家亨利-波卡雷,这些科学家都在没有刻意去钻研的时候解决了重要的问题。阿基米德发现了如何测量一个物体的体积,这是在泡澡时产生的好主意。阿基米德的发现还算是有据可查,但有些人的突破更像是“无中生有”。 数学家庞加莱曾记录过以下的经历:我对自己的失败感到厌恶,于是去海边呆了几天,又想到了别的事情。有一天早晨,我在悬崖上散步时,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简洁、突然和立即肯定地认为,不确定的三元二次函数形式的算术变换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算术变换是相同的。在这种洞察力到来之前的明显空闲期有一个名字:孵化期。如果在一个困难的问题上进行艰苦的、看似徒劳的工作之后,再进行一项要求较低的、不需要完全集中精力的活动--散步、洗澡、做饭--那么头脑就可以自由地游走。在这种酝酿中,或许能偶然发现一个解决方案。 孵化既是无意识的,也是真实的,它能切实增强创造力。在一个实验中也论证了这一观点:名大学生参加了一项创造力的心理测试,要求他们为日常用品,如砖头或铅笔找到不寻常的用途。测试开始几分钟后,主持实验的心理学家打断了一些学生,给他们布置了一个无关的任务。新的任务并不会花费太多精力--学生们会看到一连串的数字,并且被要求分辨出其中哪些是偶数,哪些是奇数,这些简单的任务分散了学生们对测试的注意力。在这一干扰之后,学生们继续进行创造力测试。相较第二组没有被分配“分散注意力任务”的学生,他们竟然都想出了更有创造力的答案。 第三组的学生也像第一组一样得到了休息,但他们得到了一个更难的任务,需要更多的注意力。结果却是,他们的答案比第一组的答案更没有创意。实验的结论是,要求不高的任务--简单到不需要太多注意力,但难到无法有意识地解决问题--可以让人的思维自由地游走,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如果走神会增强创造力,那么它的反面,即在心灵冥想中练习对注意力的控制,应该有相反的效果,包括好的和坏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例如,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心神冥想,通过减少心神游离,可以提高标准化学术测试的分数。然后,缺乏专注的人在前面提到的创造力测试中却表现更好。 显然,就像生物进化需要在自然选择和基因漂变之间取得平衡一样,创造力也需要平衡,如果在长期专注的心态下不能得到答案的话,就应该选择暂停,去玩、去做梦、去放飞心灵! 别闹了机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nxilanhaishi.com/xxlhswxtz/5448.html
- 上一篇文章: 用水枪打败秋老虎,快来棕榈泉海狮计划嗨F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