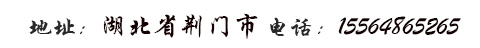从陆地到海洋库柏小说中的ldquo边
|
北京中科医院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医院订阅哦 内容摘要 探讨詹姆斯·库柏的西部小说或海洋小说时,“边疆”始终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历史地看,库柏的西部小说正是美国史学中影响深远的“边疆假说”的文学注解;同其扎根于“边疆”传统的西部小说一样,库柏的海洋小说,通过建构美国的太平洋、大西洋国家叙事来拓殖太平洋、大西洋“边疆”;西部小说和海洋小说不仅充实、强化了“边疆假说”,而且还进一步拓展了美国的疆域意识和国家意识,使其从西部陆地延展到浩瀚的蓝色海洋。 作者简介 段波,博士,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小说和海洋小说。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小说中的太平洋书写与国家想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宁波大学王宽诚幸福基金资助。 Title FromLandtoSea:FrontiersinCooper’sNovelsandtheDevelopmentofHisNationalConsciousness Abstract WheneverweexploreJamesFenimoreCooper’sfrontiernovelsandseafictions,frontierisoftenarecurringmotif.Deeplyrootedinthefrontiertraditionlikehisfrontierwritingswhichserveasliterarynotestothehistoricallyinfluential“FrontierThesis”,Cooper’sseawritings,bycreatingAtlanticandPacificnationalnarrativestocultivatetheoceanwildnessandfluidfrontiers,notonlyconsolidatesthe“FrontierThesis”inAmericanhistory,butalsoextendthenationalconsciousnessaswellasgeographicalconsciousnesstoincludenotonlythewesternfrontiersbutalsothevastfluidfrontiers. Author DuanBoisaPh.D.andprofessorofEnglishatFacultyofForeignLanguages,NingboUniversity(Ningbo,China).HisresearchinterestsareBritishandAmericannovelsingeneral,andseafictionsinparticular. Email:Duanbo nbu.edu.cn每当我们探讨詹姆斯?库柏的小说艺术时,“边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这方面的研究不少,例如斯彼勒认为“库柏是边疆精神的继承者”(Spiller26),而富兰克林也认为“边疆定居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也决定了他的眼界”(Franklin6)。尽管上述学者都论述过库柏小说中的“边疆”主题及其意义建构机制,然而他们的研究缺乏历史的眼光来观照库柏小说中的“边疆”的内涵,他们也未把库柏的“边疆”建构同美国史学中具有广泛影响的“边疆假说”放在一起进行联动考察,况且他们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库柏的西部小说,却极少论及其海洋小说,因此略显遗憾和不足。历史地看,“皮袜子故事集”同弗雷德里克?特纳为代表的边疆学派是同宗同源的:它不仅在文学和文化上为“边疆假说”做了丰富而详实的注解,而且为美国边疆的建立和边疆不断向西推进培育了人文地理想象的基因。无独有偶,在《领航人》(ThePilot)、《红海盗》(TheRedRover)、《火山口》(TheCrater)、《海狮》(TheSeaLions)等众多海洋小说中,“边疆”拓殖的痕迹也同样清晰可辨,然而这一点也往往被学界忽略。事实上,同扎根于“边疆”传统的西部小说一样,库柏的海洋小说通过建构美国的太平洋、大西洋国家叙事,不仅强化了“边疆”意识,而且进一步拓展了美国的疆域观念和国家意识,使其从西部陆地延展到浩瀚的蓝色海洋。 01 西部陆地书写:“边疆假说”的文学注解 美国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美国的边疆对美利坚民族性格、国家的形成和美国文明的发展均产生了持久和深远的重要影响。边疆史学家雷?比林顿在《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一书中,阐述边疆对美国文明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时论述道:“今天只要一提到‘边疆’这个词,对着迷于西部电影电视的一般美国人来说,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欢快的幻影〔……〕然而,在使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制度‘美国化’方面,没有任何力量比占领美洲大陆所必需的三百年间沿定居地西部边缘反复再生的文明所起的作用更大”(9)。边疆史学的另一杰出代表弗雷德里克?特纳在年发表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这篇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论文中,同样论述了边疆在美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影响:“美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片自由土地的存在,它的持续萎缩,以及美国拓殖的不断西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进程”(特纳1)。特纳特别强调大西部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认为,“要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2),因为“美国的社会发展不断在边疆从头反复进行。这种不断的重生、美国生活的流动性、西部拓殖带来的新机会以及与简单原始社会的不断接触,培育了支配美国性格的力量”(特纳2)。在特纳等人的边疆史学理论视阈中,美国的边疆主要特指大西部,因为“越往西推进,边疆的美国特征就越明显”(特纳4)。毫无疑问,正因为边疆史学家著书立说,才使得向西拓展和扩张边疆变成美国人的思想文化共识。因此在二百多年的历程中,美国不断地把边疆从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边疆拓展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边疆,直至到达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和俄勒冈,然后又进一步延伸到夏威夷、阿拉斯加、萨摩亚、关岛、菲律宾等亚洲太平洋地区,从而使得美国疆域向西延伸这一“独特性”得到进一步的显示。 毫无疑问,以特纳等人为代表的“边疆假说”为美国领土扩张奠定了思想舆论理据,然而在美国领土向西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学家并非单兵作战,同他们并驾齐驱的还有库柏为首的美国小说家。只要细读读库柏的西部边疆小说就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些小说(其实也包括他的海洋小说)本质上同特纳等人所宣扬的“边疆假说”同根同源。库柏的边疆书写在展现美国的边疆开拓者是如何征服陆地荒野(也包括“海洋荒野”①)的同时,也通过西部地理景观描摹来建构“风景的政治”(毛凌滢70),来展示边疆拓殖历程是如何煅造美利坚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是如何形成了国家意识和观念。例如,《大草原》中,欧洲的拓荒者们在“广阔的路易斯安那成为业已巨大的美国领土”(J.F.Cooper,ThePrairie9)的历史扩张时期,在“希望的幻影”和“突然地暴富的野心”(J.F.Cooper,ThePrairie11)的驱使下,在西部这片辽阔的、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上努力实现他们的“美国梦”。在《最后的莫西干人》中,哈德逊河沿岸的森林、溪流、高山、悬崖以及霍里肯湖一带的风景也得到了全景式的呈现:“广阔的”且“不可穿越的”森林里参天大树挺立(1);延绵不息的“圣水湖”绕过无数岛屿,穿过叠叠群山(2);大陆上的河水“千姿百态”,“无拘无束”(57)。在《拓荒者》中,纽约州的地理景观特别是纽约北部的奥赛格湖区(OtsegoLake)旖旎的湖光山色也得到了全景式的详尽描绘。总之,西部小说中神秘的森林、雄伟的高山、广阔的平原、辽阔的草原、平静的湖泊、湍急的河流、飞泻的瀑布,无不成为西部边疆上一个个独特的人文景观和地理标识。 库柏为何不遗余力地描摹西部边疆的人文地理景观呢?一方面,库柏描绘边疆自然景观的努力同后殖民时代的美国渴望建立一个独立的、基于“新大陆”的美国新身份密切相关;同时,库柏试图通过描写边疆定居生活来建构独立国家意识,这一点在他的书信中暴露无遗,例如,年,身处欧洲巴黎的库柏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动机与国家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时,他毫不掩饰地说:“你赞赏我的创作动机与我的祖国之间的关系,它给我带来了满足感。祖国的心理独立是我的创作目标。如果我临死时能回想起我曾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做了一点贡献的话,那我应该欣慰地知道我的一生并非毫无用处。”②很明显,库柏的创作目的和动机就是为政治服务,对他而言,写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祖国,具体讲,就是为了美国的“心理独立”和文化独立而创作。另一方面,库柏试图通过对西部边疆地理景观的全景式描绘来改造粗犷荒芜、尚未开垦的西部边疆,通过“高山哥特式”和“森林哥特式”手法来“赞美美国荒野的崇高”,③使其由原来的杂乱荒芜变得文明有序,变得更具有浪漫、高贵和庄重的气质,使之符合美国的新品味和新追求,这客观上增强了美利坚民族对北美大陆的地理认同感和国家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库柏是一名优秀的美国文学地理景观画家,他不仅为美国大众和读者呈现出19世纪北美大陆的地理景观,更为重要的是,库柏小说中的陆地风景绘制,对于引领19世纪美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来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资源,同时它也成为了19世纪美国文化独立、文化自信和国家荣誉的综合工程体系中必不或缺的要素。事实上,他的小说深深影响了19世纪前半叶美国文化艺术景观的发展。④ 总之,库柏边疆小说书写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在文学和文化上为“边疆假说”做了丰富而详实的注解,而且帮助构建了19世纪美国的文化地理景观,为美国边疆的建立和边疆不断向西推进培育了文化地理想象的基因。这些配有精美地理插画的边疆小说,配上小说主角们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气概,从而赋予北美荒寂的陆地景观以崇高和俊美的美国气质,从而为美利坚民族认同、美国身份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02 大西洋书写⑤:“海洋荒野”的拓殖 如前所述,库柏的西部边疆书写不仅是美国“边疆假说”在文学中的注解,他的边疆小说书写还是其构建美利坚民族国家意识的重要手段。可见作为小说家的库柏的确为美国边疆拓殖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如果我们对库柏的文学艺术的评价仅仅停留于此的话,那今后美国文学、文化史甚至美国边疆史研究恐怕会留下许多遗憾。一个往往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库柏不仅在他的西部边疆小说中拓殖美国的“边疆”,他甚至在他已经被忽视而逐渐淡忘的海洋小说中开辟了另一个全新的、更为重要的“边疆”——海洋。这个新“边疆”,并非仅仅包含库柏研究学者菲尔布莱克所指的文学意义上库柏“发现海洋小说”⑥,或者像学者伊格莱西亚斯所说的库柏“发明海洋小说”(Iglesias1)这个新小说类型,而且还涵盖了地理学、政治学意义上拓展新的国家疆域。因此,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库柏不仅延展了美国文学“边疆”的界限,而且帮助深化、拓展了美国人的地理疆域意识和国家意识。对于这一点,目前国内外有关库柏的研究论著中鲜有提及。 重新审视特纳的“边疆假说”,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极为严重的不足:他并没有把美国东部的大西洋纳入美国边疆体系或者美国的“势力范围”。特纳在论述美国边疆的界限时,他反复强调,“最开始,边疆指的是大西洋沿岸(4),但是,“要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特纳2),并且“越往西推进,边疆的美国特征就越明显”(特纳4)。特纳的上述论点充分说明他根本没有把大西洋纳入美国边疆的拓展范围,事实上特纳一再强调大西洋是“欧洲的边疆”,他认为美国人需要远离大西洋这个欧洲的边疆而转向大西部,进而“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特纳4)。据此来看,特纳的“边疆假说”着重强调的是垦殖西部陆地边疆,而他却完全忽视了向东开拓“海洋荒野”;很明显,他重视的是黄色的陆地边疆对美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他却严重忽略了蓝色的“海洋边疆”对美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巨大影响,这显然是他的“边疆假说”中一个极为严重的缺陷。 虽然史学家特纳忽略了“海洋荒野”的存在,但作家库柏却深刻地洞察到包括大西洋在内的“海洋荒野”同美国命运之间的纽带联系。库柏曾经在《美国人的想法》第二卷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美国人的边疆生产生活必将从西部回到东部:“西部移民大潮总会有回潮的时候,所有在艺术、生产制造、商业等各方面的探险行为都必将从西部回到东部海岸”(J.F.Cooper,NotionsofAmericansII:83-84)。由此可见,库柏“向海洋进军”的前瞻性观点恰恰是对特纳的“边疆假说”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它不仅突破了美国边疆仅仅止于西部大陆的历史观点,而且认为美国边疆范围还应该扩展到浩瀚的海洋。库柏敏锐地洞悉到未来美国崛起的奥秘:美国的未来是在大海上,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的重要舞台一定要回到东部海岸,回到大西洋(甚至包括太平洋)广阔无垠的流动空间上来。 库柏一边吹奏“向大西洋进军”的号角,一边开掘着大西洋这片“海洋荒野”,书写着美国的大西洋国家叙事。在库柏的早期海洋小说三部曲《领航人》《红海盗》和《海妖》(TheWaterWitch)中,大西洋常常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场景和重要背景。作为大西洋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海洋小说不仅组成国家叙事的重要篇章,而且也直接体现库柏拓殖“大西洋边疆”的强烈意识。《领航人》描写北美殖民地的海军小分队跨越大西洋、突袭英国北部海岛上的英军的英雄壮举。如果把小说中“偷袭式突进”大西洋的情节同库柏的海洋边疆开拓意识相提并论,那《领航人》如同其标题一样,无疑象征性地“领航着”美国人挺进大西洋的“国家之舟”。无独有偶,《红海盗》讲述的同样是美国人突破英国的封锁与包围而成功逾越、挺进大西洋的故事。小说中海德格尔无数次逾越大西洋屏障无疑也具有同样的政治文化意蕴:美国驶向“大西洋荒野”的“国家之舟”正在乘风破浪、势不可挡!由此可见,库柏的海洋三部曲无疑是美利坚民族向“大西洋荒野”挺进的历史史诗,“阿瑞尔号”、“海豚号”、“海妖号”等舰船正是驶向“大西洋荒野”的“国家之舟”。“大西洋荒野”如同西部荒野一样,成为美利坚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理想训练场,成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展示舞台;小说中航行在“大西洋荒野”上的“国家之舟”,犹如神出鬼没、行踪缥缈的精灵,成为独立、自由的美国精神的完美化身;而美利坚民族的海洋民族主义、英雄主义气概,则在领航人、海德格尔、迪勒、汤姆长子等水手的身上集中展现出来;美利坚民族崇尚冒险、敢于竞争、崇尚自由的海洋性格则通过水手们在大西洋、太平洋“荒野”上的一次次逾越而不断得到训练和锻造。 在海洋小说中,库柏通过描述美国人在大西洋、太平洋上的跨洋商贸活动来构建一个广阔的“海洋空间”⑦,以建立美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存在。《海妖》呈现18世纪初北美殖民地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景象。当时美国买卖的货物有远东的象牙,比利时梅希林花边,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绸缎,非洲的鸵鸟羽毛,西班牙的商品,以及中国福建的武夷茶。在《海上与岸上》(AfloatandAshore)中,库柏通过描写小说主人迈尔斯的几次跨太平洋-大西洋远洋历程来全景式呈现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美国的海洋开拓历程。如此一来,通过描述美国水手、商人、舟船、货物以及美国资本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流动空间上的移动或流动,若用列斐伏尔的语汇来描述的话,库柏从而“生产”了一个“表象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在这个空间里,商船、捕鲸船和水手成为意义深远的“镜像”和“符号”,成为这个“表象的空间”里的“居民”和“占用者”(Lefebvre39)。显然,正如列斐弗尔所言,库柏“描述这个空间,然而不仅仅只是描述而已”,而是想象美国人能够“体验”、“支配”、“改变”和“占用”这个空间(Lefebvre39)。从更大层面上讲,在这个“海洋空间”里,逐渐兴起的帝国通过人、物和资本在这个流动空间上的移动来不断地审视着它与太平洋、大西洋那些遥远海岛的政治关系,也正是“海洋空间”被生产的程中,以汤姆·科芬、海德格尔、迈尔斯为代表的美国水手(还包括商人、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等)以及“危机号”、“黎明号”为典型的美国商船也变成不断扩大的美国地理版图上的地理浮标,成为国家形象和身份的重要象征符号,美国形象也正是通过这些不断移动的“非语言符号和标志”而不断得到强化。 03 太平洋书写:“蓝色边疆”的延伸 及国家意识的深化 正如前文所述,库柏的西部边疆书写到大西洋书写的转变正是库柏的边疆意识和国家意识由陆地向海洋不断延伸的一种映射。然而库柏的边疆意识、国家意识并未戛然而止于大西洋,而是继续延伸到更为遥远的太平洋,甚至更广。这一点可以从库柏早、晚期海洋小说中故事场景和背景的显著差异上清晰地反映出来:早期的海洋三部曲中的故事场景大多发生在大西洋沿岸,故事的主角往往流连于“浅海”或岸上,而在中、晚期的《火山口》《海狮》等海洋小说中,故事主角不再流连于大西洋的海岸边,而是沉醉于太平洋的“深蓝”里,或是留连于当时尚未有人知晓和涉足的南极地区。小说故事场景由早期的“浅海”走向中晚期的“深海”,这一动态变化无疑也折射出库柏的国家意识由浅蓝走向深蓝并向纵深延展的变化趋势,这一变化客观上也契合美国领土向太平洋沿岸不断扩展的历史轨迹⑧。正是在美国人向“太平洋荒野”开拓扩张的步伐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以库柏、麦尔维尔为首的海洋小说家,积极投入到美国垦殖“太平洋边疆”这一神圣的“天命”中来,他们为普及推广太平洋地区的人文地理知识,为强化美国人头脑中的太平洋印象和想象而竭力做着思想文化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于是,麦尔维尔于19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接连发表了“波利尼西亚三部曲”《泰比》(Typee)、《奥姆》(Omoo)、《玛迪》(Mardi),而库柏则于年发表了太平洋小说《火山口》,三年后发表了《海狮》。 在《火山口》中,库柏的边疆意识和国家意识昭然若揭。首先,库柏在小说的序言部分就开诚布公表示要为美国在太平洋这个新疆域开疆拓土。库柏论述说,因为尽管前人,包括众多探险者已经先于他之前在太平洋地区做过许多探索,但他们“从未听说过珊瑚岛,换而言之,他们对这一区域是一无所知的”(J.F.Cooper,TheCrateri)。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库柏在太平洋新疆域的开掘是具有开拓性的。其次,库柏把自己同哥伦布、库克等欧美殖民先驱相提并论,以强调他正在努力经营的太平洋事业的开拓性和超越性, 在年,太平洋不像今天一样广为航海家们所熟知,库克虽然在二十年前展开过举世闻名的太平洋之旅,其有关太平洋的记录也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库克的记录有许多地方有待证实,尤其是其中的细节。事物的第一个发明者或者发现者往往获得巨大的名声,但却是后来之人花费精力来解释说明这些经过。尽管我们今天比哥伦布的时代更了解美国,但我们的知识还是那么的局限,哥伦布所开拓的伟大事业仍然处于初级阶段。(J.F.Cooper,TheCrater38) 库柏把自己同“举世闻名的”殖民者库克和哥伦布相提并论,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哥伦布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利益而发现了美洲,库克为了大英帝国的海外利益进行了太平洋殖民探险,而他自己则为美帝国的海外扩张事业——太平洋边疆的垦殖——也不甘落后,甚至大有超越哥伦布和库克等“举世闻名”的殖民先驱的地方。况且,在库柏看来,库克和哥伦布的殖民事业尚存诸多问题,譬如库克的太平洋探险日志有些不一定是事实,甚至有可能是虚构的;哥伦布的殖民开拓事业仅仅是开了个头,而更大的、更辉煌的成就还需后继之人来创造,而那这个后来的、但不乏超越精神的开拓者非库柏自己莫属!由此可见库柏对垦殖美国的海外疆土这一伟业是如此信心十足,同时又显现出咄咄逼人的姿态!那库柏是如何在小说中垦殖太平洋边疆,并超越欧美殖民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殖民先驱的呢?这全靠小说主人公马克在太平洋上那不可思议的拓殖行径来实现。 首先,马克以令人惊叹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信念在寸草不生的太平洋珊瑚岛上开掘美国的新边疆。当马克因太平洋商船搁浅而被困在珊瑚礁中时,他和他的随从鲍勃并非像笼中之鸟一样陷入困顿之境,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生存下来。他们先是寻找到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继而像“鲁滨逊一样垦殖开掘”(J.F.Cooper,TheCrater61),设法在这个珊瑚岛上活下来。然而这个珊瑚岛的生存现状“震惊”并“伤痛”着他们(J.F.Cooper,TheCrater61),因为岛上的糟糕状况远远比英国殖民者鲁滨逊所垦殖的荒岛条件要差千万倍,“首先,鲁滨逊拥有一个岛屿,而我们仅仅有珊瑚礁;其次,鲁滨逊的荒岛上有泥土,而我们只有光秃秃的岩石;再次,鲁滨逊的荒岛上有淡水,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最后,鲁滨逊的荒岛山有上有高耸的树木、绿油油的草,这个珊瑚岛上一束草都没有”(J.F.Cooper,TheCrater72)。总之,这个珊瑚礁的糟糕景象“用光秃秃和荒凉两个词最能确切地描绘”(J.F.Cooper,TheCrater66)。然而就是在远比鲁滨逊所处的条件更加恶劣、更加糟糕的极端环境下,马克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超人的意志,把一个根本不适合生存的太平洋火山岛开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美国“后花园”,变成美国象征意义上的海外殖民地。如此一来,通过塑造一个比鲁滨逊更加强大、更富于开拓性的美国殖民者马克的形象,库柏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活动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其次,马克还在太平洋的珊瑚岛上播撒草种子为代表的“侵入式”美国农作物,以传播美国文化。马克所乘坐的船只,本是为了美国的商业扩张而去的,是要到中国这个“异教徒”国家去从事檀香木贸易(J.F.Cooper,TheCrater25),这艘商船除了为扩大美国的海外商业利益而进行跨太平洋国际贸易之外,恐怕还履行另一项心照不宣的任务,那就是肩负播撒美国文明和价值观念的神圣“天命”,因为这艘船上装有美国的草种、西红柿种、西瓜种子等农作物。除此以外,船上还装载有猪、羊等美国的家畜。很难想象,除了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移植和推广这些“入侵者”式的外来农产品,向这些所谓的“异教徒”国家和地区撒播代表美国民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外来农作物,还存在其它的理由。因此,当马克在南太平洋的珊瑚岛上栽种草种、大豆、豌豆、玉米、黄瓜、西红柿、洋葱时,事实上他是在撒播美国文化的种子,因为没有比草种子更能代表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念,这一点诗人惠特曼已经作了精辟的阐述。在诗歌《草叶集》中,惠特曼创立了象征美国的经典意象——芳草。它们生命力强大,拥有“持久不死的根”,而且无穷无尽,“每年都会重新萌发”,会从“退却的地方再现”()。因此,只要有草的地方,就有美国的民主价值存在。需说明的是,马克的船上之所以带有大量的草种,是因为船长希望“把这些草种作为恩惠给予他想要访问的岛屿的原住民,并通过他们再赠送给今后过往的航海家”(J.F.Cooper,TheCrater87)。可见无论是美国船长,还是普通水手,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撒播美国文明的种子、传播美国思想文化的神圣“天命”。当马克在珊瑚岛上播撒下草种子后,野草在原来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珊瑚岛上遍地生长,“根也到处蔓延”(J.F.Cooper,TheCrater),最后,整个荒岛俨然一个“大草原”(J.F.Cooper,TheCrater)。正是在太平洋的岛礁上,象征美国民主价值观的草种生根发芽,并迅速蔓延到夏威夷、关岛、萨摩亚、阿拉斯加等太平洋广大地区。 再次,库柏还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民族同美洲大陆上的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等同起来,这不仅是他强烈的种族意识的表现,也是其种族归化意识的具象表现,其目的无非强调美国“白人的责任”和上天赋予的“天命”,从而为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开疆拓土和帝国事业的合理性、正当性辩护。小说中,库柏把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土著居民等同于印第安人和黑人,例如,库柏把白人水手皮特在太平洋岛屿上娶的土著女人称为印第安人,他说“皮特娶了一个印第安老婆”(J.F.Cooper,TheCrater);库柏还把土著人与黑人相提并论,例如,他问比尔,“有黑人和你一起来吗,我指的是土著”(J.F.Cooper,TheCrater);作为白人的皮特则把自己的土著妻子蔑称为“Peggy”(J.F.Cooper,TheCrater),这让人轻易地联想到英文词汇“猪”;库柏还把岛上的土著称为“野蛮人”(J.F.Cooper,TheCrater),并加上“可怕的”、“恐怖的”、“邪恶的”等前缀来修饰(J.F.Cooper,TheCrater)。在库柏眼中,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人同北美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毫无两样,波利尼西亚民族,就像美国的黑人和红种印第安人一样,是愚昧、落后的愚民,是应该被教化、征服和奴役的对象。很明显,库柏有意混淆了美国本土和海外异域的地理差异,刻意模糊了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族群同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族群之间巨大的差异,这无疑暴露了他的种族归化意识。 最后,库柏不仅虚构了夏威夷历史,他甚至还重构了美国与太平洋岛国交往的历史。这不仅是他的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策略,同时也是他的国家意识的突出体现。让我们回顾下夏威夷王朝的历史:18世纪末19世纪初,夏威夷社会在夏威夷岛的酋长卡美哈梅哈(Kamehameha)的领导下由战乱纷争的部落社会开始走向民族国家统一的道路;年,夏威夷王国建立,卡美哈梅哈一世为国王;9年,夏威夷王朝在美国的政治干预下被颠覆而沦为美国的一个州。然而在小说中,库柏对夏威夷历史的改写是显而易见的,他通过描述两个部族首领奥罗尼(Ooroony)和沃利(Waally)之间的权力斗争来虚构了王朝的权力斗争史。事实上,奥罗尼和沃利之间的斗争桥段,正是改写了卡美哈梅哈一世和他的挑战者卡赫克里(Kahekili)之间的权力斗争史⑨。不仅如此,库柏甚至还重构了美国人到达夏威夷的时间。历史上,第一批美国新教传教士到达夏威夷的时间大约在年,⑩然而在小说中,库柏把美国人卷入夏威夷历史的时间设置在年,即小说的故事时间,这比英美列强进入夏威夷的历史时间整整提前了二十多年。库柏重构夏威夷历史,并且把美国人在夏威夷群岛上的拓殖史同夏威夷的历史进行重叠交织,其根本目的,正如学者金特里所言,无非是“试图建立一种美国在太平洋存在的连贯叙述”;?他通过虚构、重构夏威夷王朝的历史,从而把夏威夷历史隐秘地、合法地变成美国国家叙事的一部分。 总之,库柏有意把美国历史同个人殖民历史相重叠,刻意把波利尼西亚民族同印第安人和黑人相混淆,故意把美国的海外殖民历史同夏威夷历史相重叠,从而使美国在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存在变成美国国家叙事的连续篇章。库柏的国家意识和帝国意识昭然若揭! 04 从陆地到海洋书写的历史文化渊源 库柏从陆地书写到海洋书写的巨幅跨越的确令人震撼,连文坛巨擎巴尔扎克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惊叹,“我无法想象《领航人》和《红海盗》同其他小说的作者竟然是同一个人!”(qtd.inDekkerandWilliams)库柏是如何做到的?这背后的逻辑链条会是什么?或许,从小说主题分析入手能帮我们揭开谜团。纵观库柏的西部小说和海洋小说,不难发现,无论是《拓荒者》还是《火山口》,都反复出现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垦殖定居的情节。例如,《拓荒者》故事一开始就围绕被射杀的鹿和坦普尔地产的所有权和归属权展开叙述;而《最后的莫西干人》更是一部记载18世纪英法两国为争夺北美殖民地的控制权而进行大屠杀的历史文本;在《火山口》《海狮》中,在海外拓殖“边疆”的主题依然清晰。这说明“边疆”拓殖和扩张一直是库柏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xinxilanhaishi.com/xxlhsbhjb/5591.html
- 上一篇文章: 萌鱼199元嗨玩福兴松鼠王国水上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